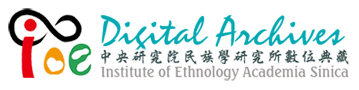祀壺之村
台灣光復前夕,1940年代的某一天,一位世居台南縣佳里鎮的醫生吳新榮,在一位平埔後裔的引導下,拜訪了「北頭平埔遺跡」。吳新榮所謂的「北頭」是現今佳里鎮鎮公所西北方一公里處,由數個砂丘圍繞,被稱為「北頭洋」的一個小聚落。在這裏,有幾戶人家還保有一種特別的祭拜行為,他們以檳榔和米酒祭拜被稱為「阿立祖」的「壺」,壺的形體一般而言,是以瓷、陶、玻璃為質地花瓶、酒瓶、或罐瓶,因此,被通稱為「祀壺」的習俗。
這類祀壺,在北頭洋以外的地方,有時壺內還插有竹蘭、菅草、甘蔗葉、香蕉葉、或芙蓉,並佩以雞冠花、黃菊花、紅圓仔花,甚至還會在壺身裹以紅布,掛上金牌者。
吳新榮將〈北頭平埔遺跡〉發表在《台灣文學》雜誌,立刻吸引了當時執教於台南、正在新化鎮知母義一帶探索西拉雅族分佈的日籍學者國分直一。他隨即拜訪了吳氏,再度巡禮北頭洋,並在《民俗台灣》上寫了一篇〈阿立祖巡禮〉。國分直一當時已知在台南州的曾文郡、新化郡、新營郡一帶的好幾個平埔聚落,都還保存著祀壺的習俗。他認為平埔族群已完全受漢族同化,語言也失去了,若能透過殘存的習俗來考察平埔族群的分佈及其與漢族之間的相互關係,當具有重大之意義。
因此,祀壺習俗的分佈就成為考查西拉雅族群分佈的重要方法,國分直一更將這些聚落稱為「祀壺之村」。不過,在這裡我們還要指出的是,事實上,在國分直一之前,移川子之藏於1931年、淺井惠倫於1938年就已先後在頭社發現有關「祀壺」的習俗,淺井惠倫並且拍下了可貴的照片。然而移川與淺井的資料當時並未受到重視,反而是國分直一的發現影響了台南地區的祀壺調查。
祀壺祭儀
每年在不同的時節,台灣各地都可以看到,人們為了社區內神明的誕辰或紀念日,舉辦各類的活動,尤其不可或缺的是那些儀式,例如道教的科儀、或佛教的法會、或村內乩童與法師的傳統、或至靈力較強的廟宇進香等等。神明聖誕的祭儀通常是一年一度的,是一種年度祭儀,而這類的年度祭儀通常是社群性的。社群性的年度祭儀不僅只是神明聖誕,還有一類是隨著宇宙時節而行的歲時祭儀,例如元宵、清明、端午、普渡、重陽、冬至等等。
台南各地區的「祀壺」信仰也不例外,但是卻有很大的地區差異性。基本上,這類以祀壺為主的年度儀式,在台南地區統稱為「阿立母夜祭」、「太祖夜祭」,而媒體喜歡稱之為「平埔夜祭」,因為這類的年度祭儀多是在夜晚舉行的。在儀式的本來意涵上,「夜祭」兼容了神明聖誕與歲時祭儀的雙重意義。
簡單地說,「夜祭」一方面是為了太祖的每年一度的聖誕千秋,另方面也隱含調節自然界與人的生活世界之間關係的歲時祭儀意涵,因此太祖年度祭儀是兩個儀式循環下所建構的。前者為了給太祖聖誕祝壽,表達對太祖的感恩與祈福;至於歲時祭儀的部份,則是人透過太祖,對生命來源的宇宙表達心中的祈求與感激,通常儀式的舉行是配合著節令來運轉的。
年度祭儀中的主神,太祖,一方面向宇宙最高的主宰「天公」,「繳旨」報告人間的禍福善惡,另一方面也為蒼生祈安賜福,因此掌管了人間的吉凶禍福。對村民而言,天公主宰宇宙間一切的生命,而太祖是受天公所託,掌管地上的一切生命,包括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有形的與無形的,因此,太祖是掌管人間最重要的神袛,僅次於天公。年度祭儀是人、太祖、與宇宙間一再重複與繁衍的調和過程。透過年度祭儀,即神明聖誕與歲時祭儀,人的存在、人與人之間、人與宇宙之間的體驗、情感、與瞭解得以產生,並代代傳承。因此,太祖年度祭儀要放在神明聖誕與歲時祭儀兩個脈絡中來解讀。
由於台南地區各地的平埔聚落都是漢人與西拉雅人的後裔所族成的,使得一年一度的太祖祭儀更為特殊,因為這個儀式過程結合了漢人文化與西拉雅文化於其中,不但形成一種獨特的地方文化,也成為台灣社會文化的一個「地方文化」。
就整個台南地區五個祀壺支系來看,其中只有新港社系沒有社群性或部落性的祀壺祭儀,太祖祭儀的舉行主要在六月十六日,但也有因配合觀音佛祖生日而改為六月十八日或是十九日,也有配合每月中旬拜土地公、好兄弟而改成六月十五日。不過,儘管新港社系沒有部落性的祀壺祭儀,新港地區祀壺的分佈可是最多、最廣。目前,台南地區祀壺祭儀的舉行主要在北頭洋社系、吉貝耍社系、麻豆社系、頭社社系等四支。
從西拉雅文化傳統的角度而言,在祭儀過程中,最能反映西拉雅文化因子影響的有三個要素:「向」、「豬」與「牽曲」。不過,每個地方對「向」、「豬」、「牽曲」方面的表現都有很大的不同。有的地方不會「說」向,就以一般的言詞說明原委;不會「做」向的就已普通的作法取「向水」祈福。若是不會牽曲,布袋戲、歌仔戲、甚至電子花車、卡拉OK都可以。有些地方不殺豬隻,就以豐富的祭品取代,祭品的多樣與變化令人嘆為觀止。
研究者與田野工作
1944年「祀壺之村」被定名之後,在吳新榮、國分直一的努力下,除了他們本人持續地在台南縣各鄉鎮從事田野工作的資料採集之外,台灣光復後,也吸引了不少南部地區的文士,例如:江家錦、劉茂源、陳春木、陳漢光等等,加入祀壺習俗的田野考察陣容。
1962年,也就在祀壺行為被發現後的二十年,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劉斌雄先生(現已退休),曾就學於國分直一先生,在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即國科會)的資助之下,針對南部地區的祀壺行為展開了全面性田野普查,包括台南縣各地與高雄縣甲仙與六龜等十六個鄉鎮。在此之前,劉斌雄曾於1957年與當時為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長、後為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劉枝萬先生(現以退休)調查過台南縣佳里鎮、新化鎮、左鎮鄉一帶。
又十年之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一位德國籍的研究人員鮑克蘭女士(Inez de Beauclair ), 於1973-1979年之間,依循劉斌雄先生的初步成果,繼續有關祀壺行為的研究,不幸鮑女士於1980年過世。之後,學術界對祀壺行為有較全面性研究的人乃是現任職於台南市成功大學歷史系的石萬壽。石萬壽的祀壺研究肇始於1979年,當時他曾陪同鮑克蘭女士於南部從事西拉雅平埔族群的調查研究。踏著劉斌雄與鮑克蘭的足跡,配合劉斌雄所惠贈的筆記與相片,過去年十多年來,石萬壽陸陸續續在台南縣與高雄縣一帶繼續祀壺的研究。結合史學的史料與田野調查的實地資料,石萬壽對西拉雅族四大社群的祀壺信仰與族群的遷移做了完整的描述與研究,集成《台灣的拜壺民族》一書。
1980年代中期以後,研究平埔文化的人漸漸多了起來,先後有劉還月、簡炯仁、吳榮順、顏美娟、葉春榮、林清財、潘英海等人投入較長期的研究。其中,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潘英海與台南女子技術學院的民族音樂學者林清財自 1986年迄1996年,陸續於台南、高雄、屏東、台東、花蓮等五縣市,從事有關西拉雅祀壺行為的研究。在本頁所呈現的資料主要是以劉斌雄、潘英海、林清財等人在台南地區有關西拉雅族的田野資料為主。
祀壺百相
「祀壺」最引人迷思的是:其所祭祀的主神是不「現身」的,也就是說沒有雕刻成體的神像金身,而是以壺、罐、瓶、碗、甕等器皿(學界習慣以「壺」簡稱各種類型)盛水於內,下鋪香蕉葉或金紙,置於地上或桌上,表徵神明的存在。不過,在不少地方也發現壺體轉化成神像,或壺體與神像並存的情形。每個「祀壺」的呈現──不論是所看到的形體與行為、或所聽到的口述資料與傳說──都是一種文化的外顯表現。這些祀壺的外顯表現(形體、行為與口傳),在每個地方所發現的,各有不同。
「祀壺」的形體
從形體的層面而言,有的是壺體裹紅布、有的瓶頸繫紅巾、有的是個碗、有的是個甕、有的瓶內插花、有的插香蕉葉、有的用檳榔、有的用香煙、有的掛豬頭殼、有的掛鹿角……不一而足。壺體的稱謂有的是阿立母、有的是太祖、有的是老祖、有的是開基祖、有的是太上老君、有的是太上道祖……也是不一而足。壺體內所裝的是水(有時是酒),通常先經過「作向」的法術處理過程,而向水是宇宙間源自於「靈」的法力象徵。
壺體內所裝的是水(有時是酒),通常先經過「作向」的法術處理過程,而向水是宇宙間源自於「靈」的法力象徵。因此,「壺」在形式上的原本意涵如同漢人民間信仰中的「香爐」一樣大,其中所盛載的是象徵著轉化人與超自然(神明、靈界)之間的力量;不同的是,「壺」的信仰叢結以「水」象徵宇宙間至高無上的力量,而「爐」的信仰叢結以「火」象徵宇宙間至高無上的力量。就像「爐」是用來裝盛神聖的「香灰」一樣,「壺」用來裝盛神 聖的「向水」。「向水」的功能與意義亦與「香灰」一樣,可以向神明乞求喝下,具有保平安的神聖意涵。如果我們瞭解其形體上的意義在於裝容神聖 的「向水」,我們就可以明白為何有壺、罐、矸、瓶、碗、甕、缸等等不同的形式;而在不同祭祀的情境之中,依實際的需求,又會出現更大的甕、缸、塑膠水桶、鋁製水桶等等。
因此,裝盛向水的容器大體上可分成兩類,一類是壺、罐、矸、瓶等瘦長有瓶肚的容器,這類大多為代表神明的壺體,有些地方稱之為「阿立矸」或「矸仔神」。另一類的容器通常所裝的只是具有保平安作用、或治病作用的向水,其容器如果大得像甕、缸、桶等,通常用於年度祭儀等人多的場合,被稱為「向缸」;如果小得像一般飯碗或菜碗,則通常用於治療性的儀式之中,我們可以稱之為「向碗」。然而,在實際的情境中,壺體因所代表的神明性質不同,外表如同「阿立矸」的壺體被稱為「太祖矸」或「老君矸」;而外表與「阿立矸」完全不同的「向缸」可能與「阿立矸」所內隱的意義相同。
由於「祀壺現相」中的神體是不現身的,裝載「向水」的容器產生神聖化的意義之後,成為神明象徵性存在的表徵,也成為祭拜者的祭拜對象。根據普查的資料顯示,大多數的地區是以壺、罐、矸、瓶等形狀之容器象徵神明的實體,但也有少數的地區以碗、甕、缸等形狀的容器為之。此外,祭拜者在不同的口述傳承下、不同的地方性集體記憶下、甚至在不瞭解原義或曲解原義之下,而產生不同的瞭解,將壺體裝飾起來,甚至近年來有不少的信徒將之雕刻成體、塑成金身。這些壺體的裝飾,通常在瓶口插以雞冠花、圓仔花、菊花、啦哩花等等一般鄉間常見的各色花種,配以作向所使用的枝葉(有如法師的法器),例如竹蘭、芙蓉、榕樹枝、竹葉、五節芒、甘蔗葉等,組成三色、四色、五色、七色、或十二色的變化。
有時,祭拜者為了美觀、或為了神聖化神體、或為了掩飾(不讓外人看見壺體),於壺體之外裹上層層的紅布,或在頸部繫上紅布條,或配戴金牌項鍊。壺體底下所鋪的香蕉葉,目前也多以金紙取代之。
「祀壺」的稱謂
上述的這類壺體或壺體所代表的神明,在稱謂上有很大的變化,但在實質的意涵卻漸漸趨於一致。根據我們在各地所收集到的神明稱謂有:太祖、案(甕)祖、老祖、姥祖、祖祖、公廨媽、公廨祖、開基祖、南路開基祖、放索開基祖、赤山萬金放索開基祖、馬崙祖、阿立祖、阿立母、壁腳(佛)仔、門後佛仔、豬仙祖、向缸祖、向祖。這些稱呼基本隱含了三類性質不同的神明,第一類是隱含以社群為主的太祖、案(甕)祖、老祖、姥祖、祖祖、公廨媽、公廨祖、開基祖、南路開基祖、放索開基祖、赤山萬金放索開基祖、馬崙祖等之稱呼;所表徵的意義是整個社群所共同祭祀的對象。第二類是隱含代表家系祖先的阿立祖、阿立母、壁腳(佛)仔、門後佛仔等之稱呼;所表徵的意義是以私人家傳為主的祖先,通常傳給長女,若無法傳給長女則長媳繼承之。第三類則隱含代表尪姨系統的豬仙祖、向缸祖、向祖、向公、向婆等之稱呼;所表徵的意義是尪姨法力來源的神明。
由於源於西拉雅的祀壺信仰與漢人民間宗教信仰的密切互動,老君、老君祖、太上老君、太上李老君、太上道祖、濾老君的稱呼已經相當普遍,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十年來,這些受民間宗教影響的稱呼,在有些地區已漸漸取代前述三類較能反映原義的稱呼。不過,這三種神明的稱謂與系統在不同地區都有不同的對應關係。
「祀壺」組成的因子
以上所談的都僅限於壺體,但是祀壺信仰的「形體現相」還包括了其他相當獨特的組成因子,使「祀壺」可以從外觀上很清楚地被識別出來,否則我們如何區辨前面所談的壺體與生活中常見的其他壺體。這些其他的組成因子,包括檳榔、米酒、竹葩(向竹)、豬頭殼(或鹿角)、以及花環等,其中檳榔與米酒是一般祭拜時所用的供品,是太祖或阿立祖的兵將所喜食用的;而豬頭殼(或鹿角)、花環、以及掛豬頭殼與花環的竹葩,則是特殊祭典後所留下來的,是具有特殊意義的神聖物品。因此,壺體加上檳榔、米酒,就構成祀壺信仰「形體現相」最基本的要件;而豬頭殼、花環、與向竹則是特殊情境下所產生的神聖物品,可稱之為「意義要件」。這些意義的形成通常都與「向」的法力有密切的關係。
「祀壺」供奉的地方
上述的壺體或神體通常被供奉在那裏呢?簡單而言,我們可以從兩個向度來解析:私家/公眾、以及地下/桌上。從神明稱謂上的三類區分,「祀壺現相」中的崇拜對象可分為社群的、祖先的、以及尪姨的。從表面的意義而言,代表社群的壺體應放在屬於公共空間的公廨,代表祖先的壺體應放在私人家屋中,屬於尪姨的也應該放置於其所屬的私人家屋。但是,實際的情形卻是相當複雜。一個社群在遷徙的過程中,若是分散到不同的鄰近的自然聚落時,或是主祭的尪姨沒有傳承下去,那麼屬於社群的壺體可能轉住到某些私人家屋,甚至消失了。而屬於私人家屋,代表祖先的壺體或尪姨的壺體,也可能因為家屋裏的某人被「牽成」尪姨或乩童、或家系中有尪姨或乩童的傳承,在開壇濟世的操作下,漸漸擁有信徒,幾個世代下來,形成屬於社區或角頭的公廨或公廟。一方面,公、私兩種系統在台灣現行的民間信仰體系的影響下,是可以轉換的;另方面,屬於社群、祖先、或尪姨等三種類型的壺體,從外貌上本來就難以辨識,使得這三類壺體的區別變成模糊不清。這些壺體,根據我們的瞭解,原先是放置於地下,通常在壺體之下置一片香蕉葉或石板,以為神座。但是,在壺體辨識糢糊性、公私轉換可塑性的認知下,為了提高神格的屬性,以免被外人視之為陰界鬼、靈之類,其最具體的行為就是將壺體提升到神明棹上。這也反映了一個事實,此三類不同性質的神明稱謂、壺體已漸漸演化成為一類,其崇拜或信仰的意義也已從「靈」或「祖靈」轉化成漢人民間信仰體系中的神明。
要之,從阿立祖或太祖放置或祭拜的地點而言,祀壺信仰可分成私家與社群兩個系統。私家系統(包括祖先的與尪姨的)的阿立矸放置在家中,一般可分為放在壁腳的(或左或右依地方習俗)和放在棹上的(即供放祖先牌位與神明的「紅家棹」,阿立祖放在龍邊),放在壁腳的又常被稱為壁腳佛,而放在棹上的通常是為了提高神格,覺得放在地上的屬陰,容易捉弄人,而棹上的則可以保家。至於社群系統的祭祀地點,通常稱為「公廨」或「公界」或「太祖廟」,在台灣光復前後,大多數都是在每年祭典前臨時搭建的,因此多是以竹枝、茅草建築而成的草寮。這些草寮基本上的意涵是神明與兵將的行館,其特色是只有後、左、右三面壁,而無前壁及前門,有的甚至於除了後壁以半片的竹草遮風雨以外,左、右兩邊亦呈空空之狀,也有些草寮是四面開敞無壁,或者附加簡易的前門以防動物或小孩入內擾亂。這樣的空間形式與有應公廟幾無差別,若不是其中的阿立矸或豬頭殼,外人是無法區辨的。之後,隨著地方經濟的好轉,加以不明每年拆舊建新的意義,所有的公廨到了七、八0年代以來,都以現代磚瓦水泥的建材取代之,但都盡力保留了原來公廨在空間形式上「三面壁」的特徵,甚至還將水泥柱與屋頂漆成竹子、木板、茅草的色彩,以表徵延續祖先留下的禮俗。
祀壺百相-北頭洋社
祀壺百相-吉貝耍社
祀壺百相-新港社
祀壺百相-頭社
祀壺百相-麻豆社
祀壺分佈與生態
 台灣原住民分佈
台灣原住民分佈西拉雅族,廣義地說,包括了分佈在台南、高雄、屏東等地區。由於學者們對此分類有不同的意見,有的人認為分為西拉雅、大武壟、馬卡道等三個族系。由於台南地區的平野昔日是西拉雅族中蕭壟、麻豆、灣裡(目加溜灣)與新港等四大社之故地,丘陵與內山則是大武壟社群分佈之故地,因此,目前對台南地區祀壺分佈的分類與歸屬,基本上都是以西拉雅四大社與大武壟社來區分。但是,這樣的歸類事實上存在著許多問題。在這個網頁的祀壺分佈,是以台南地區有關西拉雅族系的分佈為主,並將之區分為北頭洋社系、吉貝耍社系、麻豆社系、頭社社系以及新港社系。
北頭洋社系
北頭洋是現今佳里鎮西北方的一個小聚落。在這裏,有幾戶人家還保有一種特別的祭拜行為,他們以檳榔和米酒祭拜被稱為「阿立祖」的「壺」,一般皆認為北頭洋與西拉雅族中的蕭壟社群有著密切的關係。就在北頭洋不遠的地方,也就是佳里鎮、七股鄉、將軍鄉的交界處,還有兩處也保有祀壺的文化遺留,一處是七股鄉的番仔塭,另一處是將軍鄉的角帶圍。學者認為,佳里鎮、七股鄉與將軍鄉一代都是昔日蕭壟社的故地。不過,現在居住在當地的居民絕大多數都是漢裔。
此外,在東山鄉東河村的吉貝耍阿立母夜祭,每三年左右,要至北頭洋與番仔塭的公廨舉行謁祖的儀式,且每年在夜祭之後的第二天下午要為阿海祖舉行哮海的儀式,因為吉貝耍的村民認為他們的祖先來自這一帶,而吉貝耍在儀式中呼請的神明之一即與蕭壟設有著密切的關係。
雖然,今天我們從「祀壺現相」所看到的差異大於相同,但是我們仍可發現眾多聚集的阿立矸仍是蕭壟社系的特色。
吉貝耍社系
在台南平原另一處重要的祀壺地點在吉貝耍(東山鄉東河村),村中除了大公界之外,尚有北、東、中、南與東南等五個小公界以及無數的私家阿立母。這個地點一般都認為是蕭壟社所遷來的,但是研究者在東山鄉與白河鎮一帶的訪查,發現不全然如此。一則因為哆囉國社的故地即在此(東山鄉),而且也並未遷離;另則在凹仔底(東山村)的蘇家輪祀尪公祖(亦有寫成洪公祖者)與麻豆社有密切的關係,因為現在麻豆鎮的尪公廟祀有三元真君,即為尪公,此在高雄縣境內亦發現多處。因此,吉貝耍的祀壺不是那麼單純地僅與蕭壟社有關。
學者也發現吉貝耍(東山鄉)與六重溪(白河鎮)關係密切,特別是在婚姻關係方面,且昔日都是以白河(店仔口)為交易中心,屬白河生活圈的範圍。由於白河是清朝早期的交通要道之一,學者認為白河以東仍為番社之地,即哆囉國社(今東山鄉),因地處平原北端入內山的孔道,在番屯實施之後,四大社的蕭壟社、麻豆社等被派至吉貝耍屯守,這也是為什麼文獻記載乾隆年間蕭龍壟社遷往吉貝耍之主因。
不過,我們應注意的是,吉貝耍並非僅是蕭壟社的遷徙地,我們認為是哆囉國社、蕭壟社與麻豆社為主所形成的聚落(當然也包括後來的漢人)。另外,蕭壟社群的遷徙也不是指往吉貝耍的方向。學者認為吉貝耍往南沿著柳營鄉的麻埔至大內鄉頭社村的竹湖都是在蕭壟社遷徙的範圍之內。換言之,族群的遷徙是動態的,在過去漫長的四百年間,族群之間的互動早已讓族群意識語族群認同產生質性的變化,我們無法以一一對應的方式將歷史中的某一群人與當代社會中的某一群人拼湊起來。
麻豆社系
麻豆社系的分不與遷徙處要是以麻豆鎮為中心往東,經番子田(官田鄉隆本村),往社子,至烏山頭水庫一帶。麻豆鎮上的尪公廟,所祀奉的三元真君即是「尪」的拆解所組合成的意義。其附近仍住著與麻豆社通婚過的後裔。麻豆社在祀壺現相的表現相當特殊,主要是有兩個特點。其一,相當地受漢文化影響,祀壺信仰多與漢人的廟或民間信仰結合成新的合成文化;其二,麻豆社的祀壺多傾向神像化,也就是說,祀壺人家多喜將「太祖」以和漢人的神明將之神像化。此外,麻豆社相關的人家多以「尪公」、「洪公」稱呼原來的祀壺神明。
番仔田(官田鄉隆田村)的祀壺則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狀況。由於文獻上記載番仔田是麻豆社所遷來的,因此該地的祀壺常被視為麻豆社的代表。然而,歷史的變遷使得此一事實大有出入。事實上,目前居住在番仔田的舊戶人家沒有幾戶,絕大多數的居民都是在民國五、六十年代官田工業區設立之後所遷來的人口。因此,目前奉祀太祖的居民大都與所謂的西拉雅族或麻豆社後裔無關,近年甚至因為有阿美族人的移入,而將阿美族的歌舞引進每年十月中旬的太祖祭儀。換言之,祀壺的居民並不見得就是西拉雅族的後裔。
頭社社系
位於曾文溪中游的頭社(隸屬台南縣大內鄉),村內有兩座太祖公界與五戶私家阿立祖,一般咸認為與灣裡社有密切的關係。但是,在太祖公廨(太上龍頭忠義廟)的一面令旗上卻寫著四大社的社群名稱(社子社太上老君、新港社太上老君、灣裡社太上老君與蕭壟社太上老君)。根據誌書文獻、地方族譜與訪談資料,研究者指出令旗上所列的四大社名稱是深具象徵性意義的。頭社在十八世紀以前,在地理位置上是平原與內山交通的唯一的孔道。在人來人往的旺期,隨著河流沿岸的渡口與平坦地帶發展出不少的漢人聚落,如內庄與石仔瀨的楊姓、二溪的陳姓與葉姓、嗚頭的鄭姓等等。而原本沿著曾文溪於流域下游居住的西拉雅族四大社群,其中部份的族人也先後遷入頭社段丘的丘陵地帶,形成許多大小不一的聚落,如頭社、竹湖、紅花園、籠仔內、大山腳、埤仔腳與竹宅等。換言之,頭社村的西拉雅後裔並非由西拉雅族的單一社群(灣裡社)所構成,而是由蕭壟、麻豆、新港與灣裡等四大社群,以及大武壟社群所共同構成的。
頭社社系的特色在於其接收民間法師在儀式演法上的結構組成,結構完整而且具有高度的表演性。在其附近的許多公廨莫不受其影響,其影響力除了附近的嗚頭、燒灰仔、竹圍仔、大匏崙、舊社、新社、隙仔口等地之外,還影響到玉井盆地的楠西一帶,甚至還影響到屏東平原上加吶埔一帶。其最典型的影響就是在民間法師系統影響下的令旗上書寫社名。
新港社系
在山上鄉、左鎮鄉與新化鎮一帶的丘陵地帶是台南地區另一個祀壺密佈的區域,總計近五十處,昔日多被視為新港社群分佈的範圍。在此地區,祀壺的模式在外觀上大同小異,習慣在向竹上掛鹿頭殼(或以木雕代替),所為的太祖有兩種、甚至三種以上的系統,即太祖與老君,而太祖又與三十六港腳太太關係密切,因此在這個地帶的太祖常是有兩個矸子以上,或是太祖慶生有兩種以上的生日。通常新港社群的太祖生日在6月16日(616模式)、大傑巔社群的太祖生日在3月28日(328模式)、而大武壟社群的太祖生日在9月15日(915模式)。其原因主要在於這一帶是大武壟社群、新港社群與大傑巔社群的交會地帶,但是田調資料顯示329模式(大傑巔社群)是在晚近百餘年透過婚姻關係從內門一帶移出來的。換言之,左鎮/新化一帶的祀壺至少歷經了兩個時期的影響:早期(乾隆時期)新港社群與大武壟社群的遷徙與晚期(開山撫番以後)後從內門的遷出(至少是受大傑巔社群之影響)。
概括言之,新港社群的分佈主要是在左鎮/新化段丘上的群山環抱之中,以潭頂溪兩岸為主,生態相當豐茂隱密,且多竹林,是一非常適合狩獵之生態,特別是適合鹿的居住生態。雖然我們不知鹿在何時完全消失,但是我們可以比較理解為何此地的向竹之上是以鹿頭殼或鹿頭圖形取代豬頭殼。從菜寮(左鎮鄉)至隙仔口(山上鄉)一帶主要是卓猴社的範圍,有可能屬於灣裡社群,但需進一步查證。在段丘北邊的芋匏社(玉井)與東邊的木岡社(左鎮鄉睦光)則屬昔日大武壟社群的活動範圍。而段丘南邊的草山一帶是旗山、內門與左鎮三鄉鎮的分界,也是大武壟社群、新港社群與大傑巔社群往來的通道。
另外,在南化的祀壺現相也比我們原先的瞭解來的復雜。在山后林家與番仔厝黃家的訪問,我們透過族譜、墓碑與公媽牌的記載,確認了漳州人於乾隆年間入墾南化(以及左鎮)的事實。更重要的是,在南化的平埔族群因生態、交通分成三個系:一是從菁埔寮至心仔寮一帶,即南化鄉的南邊,因祀壺多受新港模式影響,我們認為是新港社往來主要的通道;二是從蘇貞埔、溪東。姜埔寮一帶,即南化鄉的北邊,因與玉井鄉的沙田和三埔、高雄縣的杉林和十張犁通婚密切,我們認為是大武壟社群的主要通道;三是南化水庫的後窟溪一帶,於日據時期才開拓,多是東大邱園與東阿里關回流移墾,亦應是以大武壟社群為主的地域。簡言之,南化鄉的平埔族群主要是以南邊的新港社群與北邊和東邊的大武壟社群所構成的。儘管南化鄉地脊貧困、窮鄉僻壤,但是在內山平埔族群的遷徙上,卻扮演了重要的折衝位置,北邊和東邊古道或山道接通了玉井盆地大武壟社群遷往高雄縣楠梓仙溪流域的孔道,而南邊銜接左鎮、新化的段丘與惡地形,引導了新港社群遷往內門之路。
祀壺人家
「祀壺」,是1940年代一個偶然機會下被發現的,並同時被視為探索西拉雅後裔分佈的一個重要文化標誌。當時,只是零零落落地在西拉雅的原鄉(台南平原)發現祀壺的村落,而稱之為「祀壺之村」。1960年代,更在台南與高雄的內山一帶發現了更多祀壺之村,這些祀壺之村與大武壟社群(被視為西拉雅族的亞群)有密切關係。近年來,除了台南、高雄之外,更多的祀壺之村在屏東、台東與花蓮被發現,有的與大武壟社群有關,有的與馬卡道社群有關。根據過去十多年來陸續的田野普查,至少二百五十處左右的祀壺之家或祀壺之村,分佈在北迴歸線二十三度半以南的台南、高雄、屏東、台東與花蓮一帶。我們所探索的已不僅只是西拉雅族後裔的分佈與遷徙。事實上,我們透過祀壺之村的分佈更加瞭解臺灣的獨特性。
然而,在「祀壺之村」的概念下,我們對祀壺行為的視角,僅是視之為探索西拉雅人的「文化遺跡」或「文化標籤」,其所存在的意義僅是文化特質、族群屬性。「祀壺之村」隱含著「文化行為」與「族群聚落」之間的等同關係,亦即,西拉雅祀壺行為的分佈等於西拉雅聚落的分佈。事實上,我們發現兩者之間的關係並不等同,而且相當複雜。根據這些年在台南、高雄、屏東、台東、花蓮等五縣市的田野普查,研究者發現各地方所表現出來的整體樣貌,存有極大的差異。
我們必須解「祀壺」,在當代臺灣的歷史文化脈絡下,並不等同於西拉雅族或西拉雅人。「祀壺現相」是西拉雅文化對臺灣本土文化的一項貢獻,這種文化現象,普遍地存在漢人與西拉雅人相互影響的地區,使得「祀壺現相」不是一種族群標誌而已,而是臺灣社會文化獨特的面相之一。
 台灣原住民分佈
台灣原住民分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