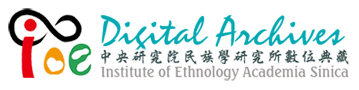災難、文化與「主體性」:莫拉克風災後的省思
蔣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
莫拉克風災過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舉辦了一場「 氣候變遷、國土保育與台灣原住民族的社會文化願景:八八風災後的前瞻性跨學科討論會」。邀集了不同學科的研究同仁,從全球氣候變遷、原住民傳統環境知識與災後遷村議題、人類學的災難研究等幾個面向進行初步的探討。這個討論會的發言記錄,已經全文刊登在民族所的網頁上,公開供各界參閱。個人負責了該討論會的籌備工作,在此謹提出一些個人在討論會前後對於災後重建議題的省思,用意在邀請學界同仁提出更多的回應、異議與討論。
“Disaster Anthropology” 基本上是一個二十一世紀興起的課題,而且相當強調自己與以往(特別是「結構功能式」)人類學研究的區別,在於災難人類學特別觀照大規模影響人類生存的「非常」事件,而非社會文化體系中「常」的過程 (Hoffman & Oliver-Smith 2002)。關於災難人類學在台灣九二一震災中扮演的角色,以及這次風災之後能夠發揮的作用,相信人類學界中對於相關議題更為專注的同仁,會有深入的討論。但是我個人觀察風災之後的台灣社會的種種言論,倒是發現在究責 (accountability) 與歸因方面,有許多值得人類學者關注的現象。在這次重大災難的背景下,這些現象透露出的,反而是台灣當前社會文化氛圍中,一些反覆出現的模式與規律。
任何具備合理資訊與知識背景的觀察者,都會同意這次莫拉克颱風之所以會造成如此重大的災害,明顯可以歸納出三個主要的成因:(一)全球暖化、長程氣候變遷所帶來嚴厲(劇烈)氣候(severe weather) 的頻繁且加劇;(二)長期以來政府對於國土保育欠缺長遠的規劃,加上以資本主義為基本理念的經營形態大舉戕害山林與海埔,龐大的政商利益糾葛,使得既有一些立意良好的法規也無法落實;(三)各級政府機構救災行動的紊亂。而這三者之中,以第三個成因「政府救災行動紊亂且無效率」,受到災民最高分貝的責難,也受到媒體最大篇幅的報導。毫無疑問,在災害發生後的短期間內,並且從災民切身之痛的角度出發,這種以直接、具象、甚至「具備人形」(anthropomorphic,例如政府首長) 的標的物為歸因與究責的對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這同時,第一與第二兩個因素,可能是災難更根本的成因,就被嚴重的忽略了。個人認為:人類學者應該有責任,對於這種面對災難時,歸因究責的模式與思惟傾向,其成因與盲點,先有所掌握,才能在更堅實的基礎上,討論或規劃後續協助災後重建的行動方案。
對於災難或不幸事件的歸因與究責,其實在人類學中有長久的研究傳統。同仁們都熟知英國人類學者 E. E. Evans-Pritchard (1937) 依據中北非洲 Azande 人的民族誌研究所提出的著名例子:人站在穀倉下,穀倉倒塌把人壓死了,人們將罹難者的死因歸諸「巫術」。這並不表示族人的思惟是「非邏輯」或「前邏輯」的,也不表示族人無視於「人死於倒塌的穀倉」這明顯的事實。巫術的歸因,處理的其實是「為何穀倉在那個時間點,當那個人站在下面時倒塌?」的問題。在像「現代西方」那樣缺乏「巫術」作為文化前提,或者「巫術」思想不具有主流地位的社會中,人們往往將這個問題歸因到「機率」;但是在許多具備巫術觀念的社會中,就會建構出:「特定的人(或某一個「具備人形」的 agent),以巫術為手段,指使穀倉倒塌殺人」的歸因論證。
巫術的歸因,相較於「機率」的歸因,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產生立即而直接的究責行動方案,讓受難者不至於徬徨無措。法國結構主義人類學者 C. Lévi-Strauss (1963) 在 “The Effectiveness of Symbol”一文中就指出:巫術治病效力的來源包括兩個主要的部份,第一是為患者的病痛提供一個結構化的解釋框架,讓患者正在經歷的原本「無以名狀」的苦難,變成可以理解的宇宙結構的一部份;第二是讓患者感到,因為苦難是結構的一部份,因此也有一套制式的行動方案,可以由擁有神聖知識的巫醫帶領著患者,按步就班的進行治療儀式,即可望痊癒。換句話說,依照 Lévi-Strauss 的這個觀點:「可理解、能行動」,就是巫醫效力的重要來源。
熟悉巫術指控 (witchcraft accusation) 民族誌的人類學者同時會想到:巫術指控的方向與對象,永遠與社會關係的結構密切相關。最常見的的指控對象,包括姻親、敵人與邊緣人等等,往往都處於結構中婚姻交換、資源競爭、或界定群體邊界上的樞紐地位。因為巫術指控與社會結構息息相關,後續的歸因究責行動方案,也就完全是一個社會層面上的修補、延續、鞏固或斷裂的過程。由這個觀點切入,我們就不難發現,在風災過後的一個月之內,災民對於政府的指責,對於政府首長前往勘災時的「嗆聲」,乃至於輿論強力提出改組內閣的要求,都極端類似英國人類學者 Max Gluckman (1963) 由中非洲的民族誌研究中提出的「反叛儀式」(ritual of rebellion) 的現象。所謂反叛儀式(或儀式性反叛),指的是在許多社會中存在的一種制式化、週期性發生的,對於掌握權力者的羞辱儀式。將台灣自詡的「民主機制」類比於民族誌中的反叛儀式,乍看不免有點跳躍,但是真正值得我們注意的關鍵點是:按照 Gluckman 的觀點,反叛 (rebellion) 不同於革命 (revolution),反叛只是在既有結構中要求人員的取代與更迭,並不產生權位結構的改造;能夠產生結構性的改變,才可以稱為革命。而行禮如儀的儀式性反叛,更有別於實質的反叛,只是具有「宣洩」(catharsis) 的作用,透過反叛儀式,壓力、憤怒與不滿得到發洩之後,包括首腦與群眾在內的整個體系又回歸到正常運作當中。換言之,反叛儀式往往更鞏固了既有的社會結構。
我之所以在這個題為「災難、究責與歸因」的小節中,大肆引用二十世紀前半結構功能與結構學派的理論(包括以結構功能學派為基調的衝突理論),去解讀莫拉克風災後台灣社會過度著重向政府救災不力究責的現象,並不是我無視於其後至晚近人類學理論的發展。而是對於這個現象的觀察,讓我感到一種「偏廢」與「保守」的憂慮。因為這種以直接、具象或「具備人形」的標的物作為歸因究責的對象,充滿了廉價的「可理解、能行動」的吸引力。讓災民與整個台灣社會,誤認為透過對於掌權者的羞辱與撤換,就算是完成了對於災難的處理。這次颱風所造成災難的規模之大,包含了其他巨大而深遠的成因,如果我們過度關注於政府救災效率方面的歸因與究責,那麼實際上是呈現出整個台灣社會仍然停留在二十世紀前半的「結構功能」時代。我擔心,這種醉心於類似巫術歸因與究責的全民運動,並不能有效的帶動結構的改變。一次又一次的反叛儀式,只會延續既有的社會結構與其中的權力及利益關係,只會保證未來災難的繼續發生,以及反叛儀式的週期性繼續上演。
風災的成因既然至少包括前述三大面向,而過度著重政府救災效率一端,進行巫術式的歸因與類似反叛儀式般的究責行動,恐怕只會阻礙我們真正需要的結構性的改變。因此,人類學者對於莫拉克風災相關議題的省思,有義務必須同時觀照氣候變遷與國土保育兩個更深遠的成因,並且在災後重建的問題上,不能迴避、懼怕整個台灣社會結構性變遷的前景,甚至要更積極的以結構變遷為目標。
在這篇短文中,我想談的革命性的結構變遷,倒不是政治或政體的革命,而是對於台灣這塊土地多年來人們習以為常的空間、領域甚至宇宙觀認知架構上,新思惟的可能性與必要性。這次的風災中,南部與東南部有相當高比例的原住民部落所受到的嚴重土石流衝擊,使得山坡地保育與原住民社會文化發展的相關議題,再度被端上台面。而在社會輿論與媒體論述當中,我也相當意外的發現一些陳年的成見與誤解,仍然瀰漫在相當多台灣民眾的認知當中。
誤解之一,可以說是「焚耕破壞熱帶雨林」論述的台灣山寨版。幾年前馬來西亞與印尼霾害嚴重,輿論大肆攻擊當地土著族群傳統的山田燒懇生計形態,認為焚耕嚴重破壞熱帶雨林,並且造成空氣污染。但是更嚴謹的環境論述立刻反擊道:跨國公司大規模的商業性砍伐森林,才是元兇。雨林居民生計性的焚耕,搭配輪耕的體系,根本不足以造成雨林的危機。莫拉克風災後,台灣也再度出現了類似的論述:「土石流的主因之一是山坡地的過度開發,原住民是山區的主要居民,也是開發這些山坡地的人,如果讓原住民全部遷出,就可以讓山林休養生息。」這個論述又可以被簡化為「封山」的口號。姑且不論這個口號背後是否有通盤的規劃,是否實際可行,類似的口號與構想本身,已經相當程度引起原住民社會的普遍憤慨與焦慮。實際上,任何對於台灣的山區社會經濟狀況稍有涉獵的人都知道,真正對山坡地的水土保持產生危害的,除了築路之外,乃是基於商業利益、具備相當資本規模的栽培(經濟作物)與經營(觀光產業)形態。這類的產業,或許也有部份原住民籍的經營者參與,但更關鍵的元素是平地的資本與市場。換句話說,這些產業絕對是台灣整體經濟的一環,而不僅僅是原住民的生計。很明顯,為了山坡地保育的目標,我們需要積極強力規範的,是一種經營形態,而不是一群人。如果台灣社會整體,以及政府的施政方針,都認為將原住民聚落遷出山區,就是最明快的解決方案,那也就無非是另一種形態的巫術歸因與究責而已。
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在同情、支持原住民的社運人士之中,存在著另一種成見,或者說是這些年來為了運動的目標,所傳誦的一套因循 (cliché) 的論述,就是將原住民呈現為安土重遷、深居簡出、世世代代與祖靈居地為伍的人群。雖然早在七0年代,美國人類學者 Roy Wagner (1975) 在 The Invention of Culture 一書中,就指出:人類社會生活中,無疑擁有「文化面向的」(cultural) 事物,也就是說,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中,許多有意義或有價值的事物是受文化層面所決定的,這是形容詞格式的「文化的」意義 ;但是作為名詞而可數的「文化」(cultures) 概念,實際上是過去人類學的一項創造 。也就是說,以往人類學者在研究的過程中,傾向於將其他人群社會生活中屬於文化面向的事物、要素,客體化成為一個個獨特且分立的文化單位,從而將諸如「排灣文化」、「中原文化」、「西方文化」等等,都想像成界限分明,高度穩定且具有體系性質的單位。雖然人類學界對於文化概念的反思,已經有相當的歷史,但台灣近十多年來,族群運動的菁英們,卻往往為了建立或強化族群認同的目的,在質疑批判人類學者之餘,同樣興高采烈的挪用著這種客體化的文化概念。於是在災後重建千頭萬緒的對話與決策過程中,我們看到一個三方盲點的大對峙:一方面是執政或決策者大體忽視文化層面的考量;另一方面是充滿善意的NGO團體將膚淺且生硬的「文化要素」(例如祭場、地標等)納入安置聚落的規劃中;再者原住民族人本身,則在面對遷村的提議時,升高了「我們可能會喪失文化這個『東西』」的焦慮感。
在民族所風災討論會中,我個人以及出席的靜宜大學的林益仁先生,都觸及了「何謂祖居地」的問題。以山田燒墾為傳統生計的原住民族群,千百年來不斷的遷徙。在某些部落的口傳歷史中,遷徙的範圍甚至不限於山區,還包括了不少明確的平地地名。而目前受災的部落位址,往往並不是歷史上可追溯的真正祖居地。實際上,長久以來,居住在現今部落的族人,就經常在平日與儀式的生活中,透過各式各樣的實踐,例如祈禱的方向、尋根的活動,和祖居地或祖源地保持著深厚心靈的連繫。那麼,受災部落族人念茲在茲的「回家」,一定是回到目前被損毀的這個部落位址嗎?可不可以是更早的祖居地呢?
林益仁先生還提出了另一個觀察:在為了山坡地保育而提出的遷村或封山意見裡,其實也隱含加深了台灣社會一個二元的成見:平地是安全的,山區是危險的。這是一個敏銳的觀察,但是,順著這個觀察,我們也發現,在原住民族人之間,也存在著一個與此相對應的二元觀念:山地是我們的、家園般寧謐的,平地是他們的、是燠熱且充滿壓力的。弔詭的是:這個長期以來台灣社會習以為常的平地/山地二元的領域認知,幾乎可以說是清代以來「番界」概念與實體的延續。雖然在日常生活中,原住民可以自由出入平地不在話下,平地居民也在一定的申請手續下,可以進出山區。但是,在全體國人對於我們所生存的這座島嶼的空間認知上,這個二分法已經被視為既定事實。除了認知層次之外,山地管制區以及山地保留地兩個制度,實質上在國有林與其他公私營事業單位的鯨吞蠶食山區土地之餘,仍然相當程度的維護了原住民族群的生計所需。但是,這種生計所賴的所有權與領域感,在山居原住民的心中,長期以來仍然籠罩著一層陰影。這層陰影來自龐大公私資本對於山區資源的覬覦,以及政府法令保障的不夠完備。近年來雖然有原住民基本法的立法,以及傳統領域調查的計劃成果,但是整體來說,原住民族群對於強勢社會經濟環境的不信任,並無法輕易解除。而這次風災以及後續的重建議案,嚴重衝擊的,就是這個長時間構築在脆弱的信任基礎上的二分架構,它既是社會經濟的,也是文化認知的。
另一方面,在部落遷址重建的協商過程中,我們也可以觀察到,外界也不應該把「原住民受災部落」誤認為一個單一的整體。原住民部落,各自有本身複雜的歷史文化、社經狀況、地方派系條件。例如最近我們得知,屬於三地門鄉排灣族的大社,與屬於霧台鄉魯凱族的好茶兩個部落,已經率先在居民共識的情況下,接受了山麓地帶移居地的安排。這兩個部落,在過去將近二十年中,因為不同的原因,已經展開了長時間自主性的遷村討論。大社是一個居住在現址超過兩百年的老聚落,但過去二十年間,因為部落上方有山岩崩塌的危險,居民也希望遷村,只是因為新址的選擇問題,尚未定案。好茶則是民國六十七年在政府政策規劃下,由舊好茶遷移而來。三十多年來,由於這個位址不符魯凱族人固有環境要求,同時生計所需土地換地的過程延宕,居民要求再次遷村,或者「重返舊好茶」的運動,正在鍥而不捨的進行當中。對這兩個部落來說,困境反而因為這次風災而獲得暫時的解決。同樣在三地門鄉,過去百年間,也有多次自發性或政策性往山麓地帶移居的例子,成效也不全是負面的。因此個人認為遷村與重建的決策,應該遵循這樣的原則:對於重建的決策與規劃單位而言,應該以獲得居民共識為首要追求目標,而且不應該以遷往山麓或平地為唯一的選項。如果在部落居民的傳統領域中可以尋得研判安全的基地,應該優先考慮。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原部落附近山區安全基地確實難尋,也希望原住民的朋友們以更寬廣的視野與心情面對新的局面。不論就學理或者就原住民本身的口傳歷史、固有環境智慧而言,遷移與文化的失落並沒有必然的關連。最近十多年來,我們事實上看到,許多原住民的文化精神與風格,也正活潑的離開山區,從各個方向進軍台灣的平地與都會。此外,正如同近年來我們透過不同媒介,極力宣揚的:南島民族擁有的本來就是一個無所畏懼、航向未知、征服大洋的文化傳承。正因為如此,南島民族才有可能在數千年前,就由台灣(這個可能的原鄉)出發,逐步踏上所有東南亞以及太平洋的島嶼,成為世界上分布最廣的族群。
如果我們可以用想像力與創造力來領導法規政策與政經架構,而不是讓法規政策與政經架構限制創造力,我願意想像一個南部(甚至全台灣)山區新的空間架構:(一)國有土地大量的釋出,讓大批原本在部落附近或山麓地區,族人豔羨但不可得的國有林或台糖的土地,都能夠為族人所使用;(二)在族人的充分認知與同意下,撤離有土石坍方立即危險的部落位址;(三)遷至山麓的部落,在自我意識的建立與法規制度的配合下,形成全新意義下守護山區林野的「隘勇線」,面對平地,負責阻擋商業資本與不當政府建設案對山林的入侵,這是原住民領域向山麓與平地的推進,而非退縮;(四)最後是在完善法律的規範下,保障各部落對於「傳統領域」一種集體文化、儀式、精神上的產權,而將遷居後新址周圍的耕地,作為生計所需的資源。這些想像或許過度理想,勢必需要克服重重的困難,才能實現。這讓我想起來義排灣族的一則洪水神話:
洪水過後,地上多石而無土,分散的族人中最後走的老大,就將洪水後掛在樹上的蚯蚓放在地上,使之排便,所排之便就變成山脈與平原。由此所生之地便全歸 Ruvaniau 家所有,這就是為什麼大頭目家有許多土地的由來。
這一則故事給我們的教誨,並不是蚯蚓可以產出山脈土地,它真正的精神是:洪水過後,正是重新開始的契機。正如同許多原住民洪水神話的情節所傳遞的訊息:洪水過後,重新獲得火種,重新繁衍生息,重新發展文化,重新組織人群。台灣原住民的文化生活,絕對不是一般刻板印像所認為的千百年來停滯保守且一成不變。在這次的洪水過後,一切大膽創新的想像與策劃,由此開始,有何不可?
「在這次的研討會中,沒有學者能明確地跟我們說什麼時候可以回家去。我想說,那是我從小長大的地方,我的家並不危險!」
「我們的心聲很簡單,就是我們要回家,請大家尊重原住民的主體。」
「我們今天作為原住民同時也是災民代表,到這裡來希望強調的是『回家』的主體性。請大家時時刻刻提出建言時,都要考慮到這個問題。畢竟,我們已經歷過太多的『被決定』」。
上面是「南方部落重建聯盟」幾位年輕的成員代表,在民族所風災座談會上的發言。這樣的論述,相當程度也呼應著近年來持續進行中的三鶯與溪洲部落反拆遷抗爭,其中主要的一個論點:「雖然縣政府認定這裡是行水區,但根據我們的經驗與判斷是安全的。沒有人會拿自己的身家性命開玩笑。」三鶯溪洲的案例背後,當然有著都市原住民的血淚,以及政府政策與執行上的疏失,但是「這個地點究竟安全不安全?」「他們為什麼一定要住在有危險的地方?」也確實是台灣大部分民眾心中的困惑。同樣的隔閡與猜疑,在這次風災後,再度浮現並且加深。
作為人類學者,我們當然高度理解並支持原住民社會文化「主體性」的追求。我們長期面向主流社會鼓吹對於弱勢群體、另類文化的尊重與瞭解。不論這種正義感是來自一個稍嫌天真樸素的文化相對論信念,還是一個社會改造的浪漫熱忱,在絕大多數場合,選擇站在另類與弱勢的一邊,仍然是人類學者神聖且嚴肅的自我期許。但是,如果當前災難的成因當中,長程全球氣候變遷造成嚴厲氣候的頻繁與加劇確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那麼我們必須謙虛的承認:面對大地的反撲,任何「人」都沒有辦法也不應該奢言「主體性」。過度相信人類的主體性,不正是工業革命後三百多年來,人類以「征服」與「開發」為價值,過度使用化石燃料 (fossil fuel), 導致全球暖化加劇的基本信念嗎?雖然在追求環境正義的長遠目標上,我們主張應該透過國家或國際社會的力量或者機制,懲罰環境的加害者、扶助環境的受害者,但是針對眼前的困境,所謂「不願面對的真相」,可能真的是不分強者、弱者,加害者、受害者,都真的必須面對的真相。而在這個真相面前,我們都必須要收斂我們的「主體性」。
所以嚴格說來,很明顯的,「主體性」只能是一個社會文化領域的觀念,而不是地球科學領域的觀念。只有在這一層認識上,我們才可以進一步釐清問題的癥結,這個癥結就是「知識的政治與權力」。面對這個問題,人類學者的處境有點尷尬。我們的學術傳承,基本上習慣於平等對待所有不同的知識體系。在人類學者眼中,所謂「西方的科學」,也不過是發源於特定社會、特定歷史脈絡中的一套文化體系而已。何況在許多在地 (local) 及微觀 (micro) 的脈絡中,西方科學知識確實並不見得比在地知識來得優越。那麼,我們是否可以秉持一貫的信念,在對於環境中危險因素的判斷上,也支持族人在地的知識傳統,拒斥源自西方的科學判斷,藉以彰顯受災部落的主體性呢?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在降雨量趨勢判斷、山坡地地層與岩盤穩定性鑑定等等問題上,在地知識可以補科學知識的不足,但是不足以取代科學知識。不論科學知識的傳遞過程是否籠罩著種種壟斷與權力的操作,也不論是否如俗民方法論 (ethnomethodology) 者所強調的:精密科學從業者對現象最基本的觀察工作,所依賴的感官能力,其實與俗民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能力,並沒有本質的不同;我想即便是人類學者,也不得不同意:一個能夠把人送上月球,再安全帶回來(雖然偶而也會出錯)的知識傳統,在對於物理世界的理解與預測上,應該得到更多的信賴。
因此,包括受災部落的族人以及台灣的一般民眾在內,我們都應該更清楚的認識到:災民單純的「家園」觀念,以及主體性的強調,並不是也不應該是對於科學知識與判斷的顢頇抗拒。人們抗拒的不是「科學知識」本身,而是「知識的權力關係」。在知識的政治或者知識的權力架構中,科學家的地位等同於社會中的祭司,肩負著解讀天象訊息的責任。在所有社會中,祭司都是社會體系中重要的一環,或許很崇高、或許刻意處於邊緣,但始終都會透過明確的儀式過程,將他們所解讀出來的訊息,轉化成為人們社會生活中內建的一環。我認為在這個觀照下,原住民受災部落人士口中的主體性,爭執的焦點就應該落實到:「我要相信你們社會提供的祭司,還是要相信我們自己社會的祭司?」或者進一步:「我是否應該抗拒一切祭司(把解讀天象的能力視為神聖而神祕的知識且加以壟斷的人),只相信我自己個人的判斷?」或者更根本的:「我們屬於一個社會還是不同的社會?」等問題的層面上。
既然釐清了爭執的焦點在於「知識的權力關係」而非「科學知識」本身,那麼以跨人群相互了解、跨領域傳譯溝通為己任的人類學社群,就應該對三個方面都展開大聲的呼籲:
(一)對於台灣社會大眾:我們呼籲要體認受災社群的堅持與對知識權威的質疑。他們並不是僵化的固守「傳統」或「迷信」,抗拒科學的判斷及預測;他們要求的是更開放、平等、對話的知識交流與決策形成的社會過程 (social processes)。
(二)對於掌握相關科學知識的學術與政府部門:我們要呼籲致力於建立並承認「科普團隊」的重要性與專業性,將科學的預測與善意的警告,透過社會對話的過程,與不同族群的民眾溝通。並且要在過程中傾聽、吸納在地的環境知識。
(三)對於受災部落的族人:我們要呼籲思考「主體性」的彰顯,並不在於抗拒大地的變遷,也不在於抗拒科學所提供更精準的知識。而是在於以傳統在地知識為基礎,以開放的心胸考核、取用來自其他傳統的知識與判斷。台灣原住民族群中,無處沒有大洪水災難過後,人群重新生息,典章文物制度推陳出新的傳說故事。在面對不可避免的環境變局時,發揮固有文化所提供的創造力,以「番刀出鞘」的氣魄,迎戰新的生活,這種精神本身就是台灣原住民「主體性」的展現。
Evans-Pritchard, E. E. :1937 Witchcraft, Oracles and Magic among the Azande,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Gluckman, Max :1963 Order and Rebellion in Tribal Africa: Collected Essays with an autobiograph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Hoffman, Susanna M. and Anthony Oliver-Smith eds. :2002 Catastrophe and culture: the anthropology of disaster. Oxford: James Currey.
Lévi-Strauss, Claude :1963 The Effectiveness of Symbols, in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Claire Jacobson and Brooke Grundfest Schoepf, New York: Basic Books.
Wagner, Roy :1975 The Invention of Culture,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